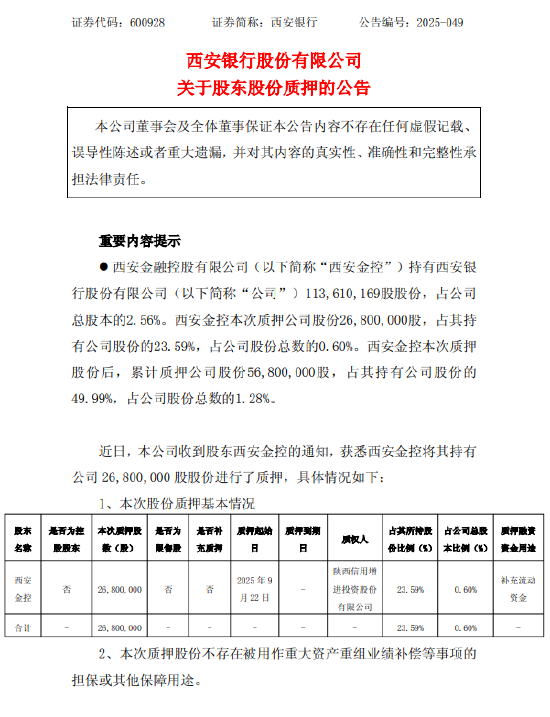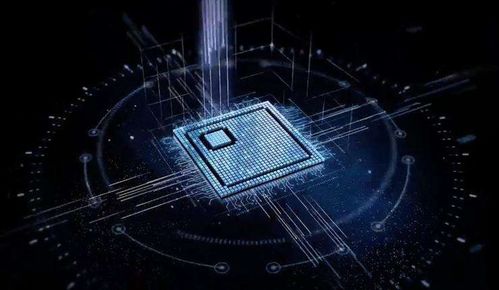美国外交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其对外关系的具体行动上,更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应对策略的新尝试。
这一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对历史的回归,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曾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分为四大流派: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对邻国的强硬态度,与汉密尔顿主义强调的经济保护主义和联邦政府对商业的介入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回归历史的行为,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某些传统元素的复兴。
从内外政策的联动来看,这些变化本质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旨在维护当权阶层的利益,特朗普的关税战、移民政策以及对特定行业和个人的政策倾斜,都是其回应国内特定利益集团诉求的体现,这种政策调整虽然打着“维护美国利益”的旗号,但实质上是对国内政治生态的回应。

从国际变局的视角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变化是其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的新路径尝试,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全球秩序的变迁,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寻求新的政策路径来维持其霸权地位,这种尝试反映了美国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和对政策调整的迫切需求。
这些政策调整能否支撑美国的“霸权”地位,效果仍存疑,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不屑一顾、对利益交换的依赖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国际社会的“疑美论”,这不仅对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度造成了影响,也对其国内治理和国际政策协同带来了挑战。
美国外交政策偏好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既是对历史的回归,也是应对国际变局的新尝试,这些变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地缘布局以及外交风格都将产生深远影响。